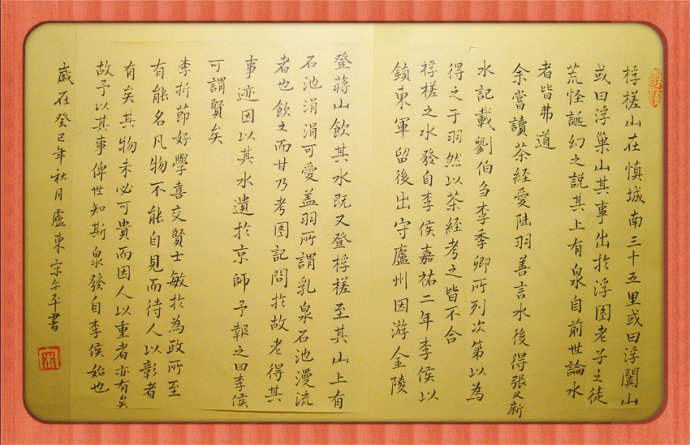摇滚青年:
你好,摇滚青年,2008年的时候我在WH市,那时候青春躁动,春心思潮,在QR我认识了一个长的瘦瘦长长,尖嘴猴腮的哥们,我称他为三哥,有一天晚上我和他谈起了Beyond,那时候屌丝的我物质匮乏,精神面接触到也都是港派台客,他说你可以听听唐朝“我十三岁在家听他的歌觉得太牛,有一段时间老是在房间中唱《九拍》,我妈觉得我神经病”,后来我在傍晚的网吧中搜到《九拍》,太他妈难听,我说太硬接受不了,鬼哭狼嚎不是我喜欢的风格,那时候他坐在我旁边,用电驴自由版搜索吉尺明步,侧过头来告诉我那就试试《梦回唐朝》和《月梦》,我一听,操,风花雪月和中国风原来从唐朝就开始了,我说不错这是我喜欢的风格,他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在网吧的东北角一台十四英寸LCD纯平显示器上观摩《江湖四十八式》,入夏时夜晚的灯光从街上照进来,天空中炊烟弥漫,灰蓝色的天空微弱的彤云逐渐散去,后来我们走了出去,在香樟树浓荫洒下来的小道,他告诉我唐朝的主音吉他手张矩,“亚洲第一快手”,死了,后来我就不怎么听唐朝,他抽着五块钱一包的红梅像大多数装逼的老师傅一样对我指点江山,崔健和一帮所谓的中国摇滚领军在德国柏林开演唱会也就那样,他说,中国没有好的摇滚,土壤不合适,80年代刚刚有点起色,你看,现在满大街口水,刀郎和庞龙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你可以尝试听听枪花、涅槃和绿洲。
为了发泄躁动不安的荷尔蒙和提升逼格,我开始顺着他指引的方向,一个夜雨的晚上,百无聊赖,我突然记起了GunsNRoses,雪地秃鹫,乳房和枪,两个争风吃醋的女人,站在悬崖边的Solo,高抛起吉他转身离去,年迈者拄着拐杖站在墓地,蓝色眼睛的婴儿水中浮起,这些意象一瞬间吸引了我,那时候我有一部1GB闪存卡的TCL手机,只支持3gp和低帧avi格式,我小心翼翼将已经烂到极致的flv格式转码,身体钻到桌子底下,冒着时常被静电震的虎躯一动的风险找USB借口下载,反复听,从《don’t cry》、《november rain》、《patience》到《knocking on heaven’s door》,几乎每首歌的循环次数都在100次以上,这也导致了我后来的恶习,我总是将特别喜欢的歌听到吐为止,当然这也有一点好处,就是过了几年当你走到大街上偶然听到一首属于这其中的一首你会莫名想起曾经的一段时光,如果那时候的味道恰巧对,无疑你会坐在街角莫名感伤一番。
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逼格已经提升到有一点档次,在回去的路上,我总是有意无意的将话题朝这方面勾引,我说枪花虽然不错,但是离Nirvana还是有一点档次,那种精神的孤独无助,嘶哑的嗓音,演唱会最后的愤怒,我总是情感多于理智,我说我还是比较喜欢Nirvana,三哥笑了从不与我争辩,又开始兜售卡百利和山羊皮,一段时间之后又换成Metallica和Dark tranquility,再之后是Rolling Stones和The Beatles,最后他说听Bob Dylan吧,推荐的理由竟然是他是一位诗人。
Bob Dylan之后我离开了QR,过了一段孤独寂寞的时光。有一天早晨,我在一间十个平方的房间中醒来,阳光照进贴满防尘红色薄膜的墙壁,我感到绝望,风摇摆着树叶在我的窗前,我裸露着上身坐在电脑前,有一台电脑城200块的低音炮,我将旋钮调节至最大,电脑音量调到最大,播放软件的EQ均衡器+20DB,听了半个小时唐朝的《国际歌》,尽管在这期间我隐约听到有人在楼下朝我怒吼说孩子高考,我没理会,直到证明了200块的音响的确经不住折腾,我操了一句娘,在如烟的六月走到蓬莱路。
这里一定有出路,小丑对小偷说
现在实在太混乱,我可轻松不来
商人,喝我的酒,犁人掘我的地
但他们没人识得这些的价值所在
没什么可兴奋的,小偷他侃侃而谈
咱们之间好多人都觉得生活只是个玩笑
可你我,都是过来人,我们的命不该这样
所以我们别再夸夸其谈,时辰已经不早
沿着瞭望塔,王子注视远方
女人们来来回回,仆人打着赤脚
城外远处有只野猫在怒号
两名骑士马临城下,狂风已在咆哮
—Bob Dylan《All along the watcht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