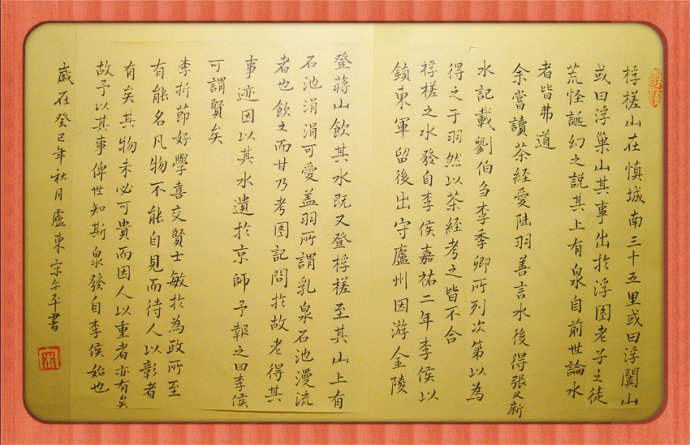
小时候每逢元宵节都有登山的习俗,所登之山就是这浮槎山,《博物志》记载天河与海相通,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浮槎”之名便由此而来。元宵节早晨七八点光景,和同村的小伙伴相伴,浮槎山中有一座甘露寺,俗名“大山庙”,说是地藏王菩萨的九华山最后一座道场,按理说这应该是一座佛庙,一进山门前有弥勒后有韦陀,左有东方持国天王多罗吒,持琵琶,南方增长天王毗琉璃,右有西方广目天王留博叉,持蛇,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持宝伞,走进别院,左别院供奉着观音和金童玉女,这些都无可厚非,但是右别院供奉的却是道教的三清,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但是考虑到佛教“大开方便之门”,求子拜观音,占卜求三清解决供需也能理解。这甘露寺通常是每次登山的目的地,一般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顺着桃花庵而上,穿竹林,过茶厂,经茶林,山势较缓比较近便,另一条要翻两座山,过一条长约一公里的峭壁小径。
到的庙门的时候以前1-2元,现在大概有5-10元的门票,不过我们时常都是走后门迂回进去,进去也不烧香也不拜佛,就是瞎逛,听老和尚给人家解签,记得有一次的老和尚给一个解签,那个人说曾去过普陀,普陀是观音的道场,那老和尚立马施礼,但是我时常怀疑这老和尚不守清规,我曾不止一次两次在后山或者小树林里见到肉骨头,因为庙也不大,伙房在三清旁边,我好几次有冲动想窜进去看看。还有老和尚也不是真光头,带着个帽子,我也不止一次看到脑后门发青的毛发蠢蠢欲动,解签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签通常是一首没有平仄的七绝,右下角注着是什么品级的签,如果是上上签就得另外加三十,如此这般。据说现在此处要被改造成旅游区,庙再盖大一点,老和尚估计也要换岗。有时候我就想,要是我学历再高点,学个专业,我就过去坐地起财,什么也不干,就给人解签,上上签、上签、中签、中下签、下签、下下签我按照50%,10%,10%,10%,10%,10%配比一下,我就发了。 继续阅读


